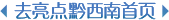第二堂课,到另一个镇,一位男老师太紧张,从讲台上摔了下来。
西安小学的许海英老师因为压力太大,几夜睡不着,上课时嘴上全是泡。
李俊小学的侯建侠老师倒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语文老师,刚开始对课题也非常感兴趣,被课题组给予厚望。后来她发现,20分钟时间总是讲不完那些知识点。有一天,她发邮件给课题组,第一句话就是“我做不下去了,有没有现成的教案,我实在设计不出来”。
课题组的专家收到邮件,心里一惊,“连最好的老师都崩溃了?”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最初的几个月,作为海原课题组组长的马兴旺心里也没有底。在何克抗和课题组专家的指导下,师生们的长进却似乎并不大。
“这一年如果没有成果,我们就真的拿老百姓的孩子做了试验。”马兴旺在心里问自己,“咋能拿老百姓的孩子做试验呢?”
眼见着好多老师都打在退堂鼓,他又要不断地为老师们打气。怀疑者也不少。宁夏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张玲和她的研究生们也是海原课题组的成员,她发现,有时何克抗不能亲自来海原,由课题组里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代表,有些人就质疑,这些没有教学经验的“娃娃专家”能否指导一线的老师。
但最终消弭这些分歧的是某种精神力量。从何教授到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从海原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到北京来的“娃娃专家”之间,这种力量始终在相互感染着。
钟林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北师大的吴娟博士走到为她准备的木椅前,椅子上有灰,吴博士绕到另一侧才把灰尘吹掉。钟林意识到,如果刚才顺势一吹,会吹到前排的孩子身上,绕一圈就吹到了走廊里。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钟林说,“这种对孩子的爱是共通的。”
爱和耐心的等待最终有了回报。课题实施5个月之后,有消息传来,树台中心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学生编了个字谜,“渐”是水车千斤重,后来关桥中心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学生说,“棉”是树上挂着白毛巾。
在《四个太阳》这篇课文的写作环节,一个一年级孩子写道:“我想有个黑色的太阳,黑黑的太阳能把奶奶的头发晒黑。”还有一个孩子写:“画一个爱心的太阳,送给玉树的小朋友。”
在海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很多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也没有见过像这样富有想象力和丰富情感的一年级学生。
这些变化促使教师们更加热情地投入到课题中。难堪的第一课之后,田虹老师住到了学校里,先后写下了4本教学反思。有一天晚上11点,钟林正在办公室写博客,听见楼道有声音,有点怕。仔细一听,“哦,是田虹在读课文”。
56岁的范有邦是课题组中年龄最大的老师。刚开始这位老教师连电脑怎么开都不知道,后来为了多媒体教学,他买了一台电脑,誓言要给自己的教育生涯画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侯建侠也终于能够掌控跨越式的课堂,被人们尊称为“大侠老师”。
海原试验班和非试验班的对照成绩显示:半年时,差别不大;课题实施一年之后,试验班的语文平均分高出了10分,而且越来越接近县城学生的母语水平。
在一次总结会上,马兴旺有些动情地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谁教育了我们?是我们的孩子教育了我们。是谁鼓舞了我们?是我们的孩子鼓舞了我们。”
跨越是为了同一起跑线
今年6月,实施了近一年的海原课题在西安小学召开了一次现场会。与会代表听完两节语文课之后,刚调到教育口不久的海原县教体局局长白旭代表主办方发言。
实际上,这位局长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课题。他没有念别人事先拟好的讲话稿,只想“说说心里话”:“我们看惯了现在社会上的种种"作秀"。最初我在看到会议指南上的学生作品时,怀疑这些并不是学生的真实作品,或许是学生家长写出来的。”
人们这才想起,此前在观摩现场课堂教学时,白局长始终在用质疑的眼光观察学生的写作过程。他接着说:“当我看到学生一边思考一边写作,写一会儿想一会儿,写错时还不停用橡皮擦了重写,我才相信这些作品是真实的,是学生在课堂里真实的生成。一年级的娃娃就能写出这样好的作文,这真让我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