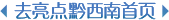这是一则童话,大意是:春天,小柳树长出了叶子,很得意,由此就看不起光秃秃的小枣树。到了秋天,小枣树结了许多又大又红的枣子。小柳树看看自己,什么也没结,这才意识到错了。
与城市里那些精心准备的公开课相比,许海英老师的课看上去并不热闹没有调动孩子兴趣的多媒体课件,没有新课程改革提倡的互动式参与,也没有衍生出来的拓展内容。唯一不同的是,她使用了一种被称为“211”的教学模式。
一节课40分钟被分成三部分。前20分钟是老师对课文的讲解,随后让学生们翻开一本由课题组编写的《拓展阅读材料》,课本里的每篇课文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的6~8篇拓展阅读文章。就本篇课文来说,有儿歌《树》、散文《小柳树》、成语故事《囫囵吞枣》,还有一些主题与课文相似的童话,如《8支荧光笔》《文具盒里的小故事》《太阳和北风》等。许海英挑出其中5篇,要求同学们快速阅读,不认识的字,自己查字典。
大约10分钟之后,许老师宣布阅读结束,然后在黑板上出了两道作文题。一是描写一位好朋友,要注意发现对方的长处,二是续写这个寓言故事,两题任选其一。这个10分钟的写作环节就是让学生尽量写,最终是否写完并不重要。
“一个好的思路,其实往往很简洁。”一位一直在关注这项课题的老师评价说,“在小语界,老师们公认阅读和写作很重要,但是很少有人敢于砍掉一半的教学时间,让低年级的学生自主地去读和写。”
对于许海英老师的这节课,何克抗认为还有提升的空间。他一直在掐着时间。由教师主导的教学环节用了27分钟,这导致以学生为主体的扩展阅读和写作分别仅剩下6分钟和7分钟。何克抗认为,原因在于许老师对教学目标的重难点把握还不到位。
有一个环节,许老师提问,小柳树怎么好看,谁来读一读?小枣树怎么难看,谁来找一找,读出来?这段提问加读书用了5分钟时间。
“传统语文教学的弊端就在于,把80%的工夫用到了不必教的地方。”何克抗说。这两个浅显的问题,学生读过课文就能解决,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相反,教学重点和难点在体现语文人文性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上,比如如何引导学生意识到,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取长补短。
海原县教研室的一位老师听完之后频频点头。他举例说:多年来,老师们教《将相和》,都是从一开始就提问,渑池会上,廉颇怎么样?学生照着书回答,“廉颇是……”接着,老师又问蔺相如怎么样,秦王怎么样,从头问到尾。看起来师生之间是有互动的,结果是学生一无所得。
要是按照跨越式的理念,老师在备课时就必须抓住重点。比如《将相和》的特点是通过外貌和动作来反映人物性格,那么20分钟的教学就要引导学生通过语言动作外貌去体会人物性格,随后10分钟拓展阅读都是关于人物的短文。最后10分钟的写作环节,可以让学生们写自己的同学,要求通过外貌、语言、动作来反映性格。
在海原,一天的工夫,何克抗和课题组成员跑了两所乡镇中心校,听了4节课,评了4节课。回到县城宾馆时早已天黑,就在等待服务员开房门的短暂工夫,年过七旬的他斜倚在服务台上,一言不发。
“老先生累得够呛啊。”随行的海原老师们私下感叹道。
找回孩子们的创造性和人文性
时光倒退50年,当年轻的何克抗在北师大物理系学习电子专业时,一度痴迷于写小说,甚至一心想转到中文系。后来转系未成,留校任教。1979年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北师大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成为中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开拓者,一生都在琢磨怎样把与教育有关的那些理论、技术跟实践相结合。
他从未放弃对母语教学的热情。“中国的语文教育多年来存在三大问题。”何克抗后来总结道。一是过分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而忽视其人文性,二是过分强调标准化考试而窒息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三是过分强调写作技巧的训练而忽视对学生观察力、想象力的培养。
他服膺老一辈语文特级教师于漪的话“学语文就是学做人,伴随着语言文字的读、写、听、说训练,渗透着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母语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系统,而是牵系着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何克抗看来,这就是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不认清这种人文性,只片面强调语文的工具性,用手术刀对文章肢解,留在学生脑海的就只能是鸡零狗碎的符号。这样做的后果是,“把学生的思维捆绑住了,把活生生的学生变成机器人,把学生的个性、灵气都给打掉了”。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何克抗就下决心要把孩子们的创造性和人文性找回来。